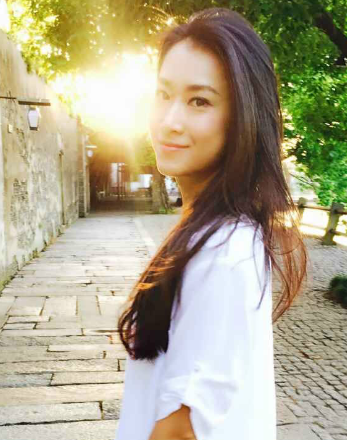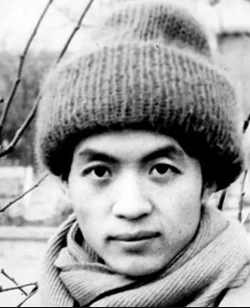读库2104简介
《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是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摄制组跟随作家莫言数次回到高密,并赴龙口、长岛、济南等地拍摄,以及在北京进行访谈之后的整理稿。导演张同道跟莫言聊故乡、聊童年、聊父辈、聊成长,同时聊作家一系列作品诞生的故事以及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影响他的人。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作家,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历史用文学的方式,给它一个记录。在访谈最后二人谈到诺奖,莫言说一个作家最终真不是靠数量,而是靠作品的质量来取胜的。
《母亲的病》是一位九零后作者对自己家庭的记录。母亲操劳大半生,一直为疾病所苦,头痛、高血压、贫血、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更年期综合征、肌肉疼痛等等。全家人因为母亲的病痛四处求医问药,母亲自己几乎到了乱投医的地步。从这段2017年到2020年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县城普通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的生活变迁。
电影海报既可以说是所有视觉艺术...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