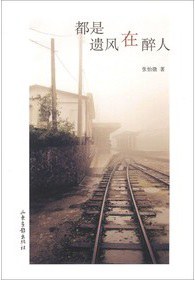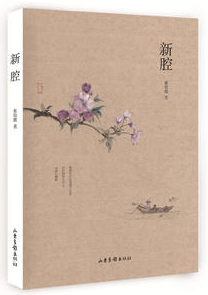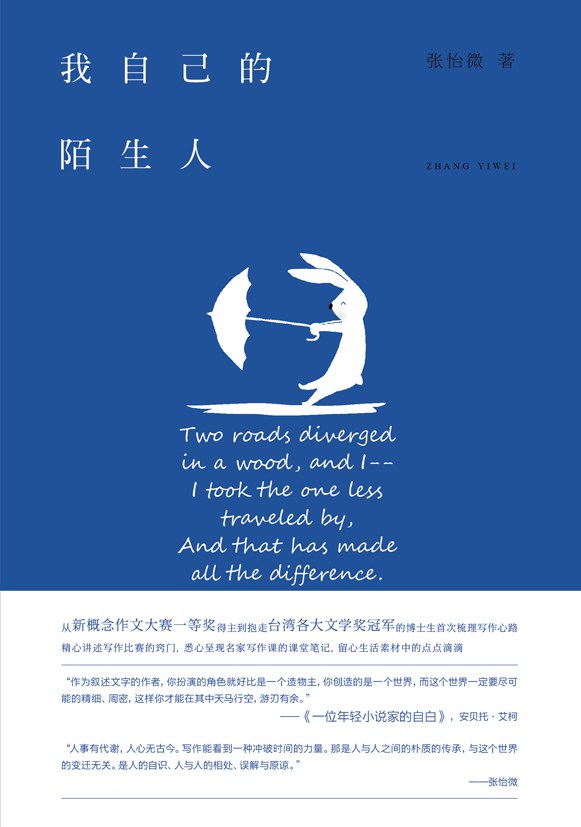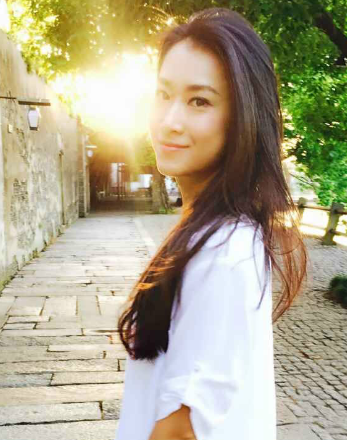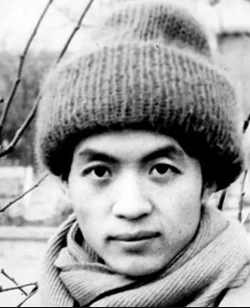都是遗风在醉人简介
本书是上海才女作家张怡微在台湾生活三年的图文集,是典型的的“异乡人手记”,是往返于上海与台北间的“两地经验”。作者以细腻温情的笔触描绘台湾,以文艺的情怀行走在台湾的路面,感受梦想与现实中这个艺文所在地的灵魂,涉及文艺青年所钟情的台湾在地风情,记叙余光中、吴念真、舒国治、林汉章、骆以军、周梦蝶、九把刀等台湾作家、诗人、电影人的行迹以及融化到骨子里的生活琐碎中的“这些人,那些事”,从“水城”台北到《悲情城市》中失语的九份,从莺歌老街到鹿港小镇,那满溢茶香与书情的永康街,那充满古早味的大稻埕,那犹如进入玲珑宝盒、充满惊喜与生趣的中山北路……也许,这从地表渗透出来的来来往往的市声才是台湾最美的风致。
台北就像是所有非台北人的一个梦,仿佛远离生产,充满诗情,有着闲散的下午与无穷无尽的温暖音乐、宜人文字。但事实上,这样的台北可能是在地的台北人都不尽熟知的自身,与我们所亲手建立起的文艺台北相比,现实也许不那么纯粹。从上海到台北,从文艺到真实,从风景到人情,曾经的盛景、幻影都宛若轻烟,折射着旧日的旖旎与温情。都是遗风在醉人。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