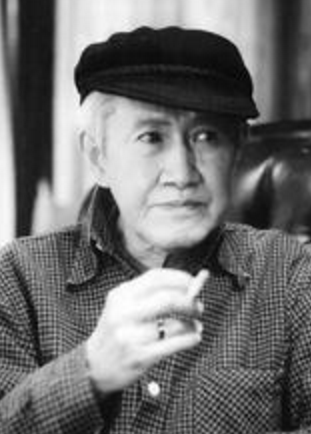三十三年前我游访洛阳,夏季,河南一带赤风刮地黄尘蔽空,真不敢相信要建都于这种地方,我的意思是黄河流域的天时确是大变了。后来回江南与朋友谈起,他说:“洛中何郁郁。”公元二百年之际洛阳是草木葱茏,非常宜人的。我笑道:“郁郁”是指人文荟萃,不过一千七百多年前那边的气候,大概和现在的杭嘉湖差不多。龙门石窟可说是健在的,论整体的艺术水准,山西的云冈石窟尤其自信、元浑,一派概不在乎的涵量,龙门就在乎了,著名的交脚菩萨可比世家子弟,清秀,一清秀力道就差下去,菩萨和人同样,清秀是衰象,而龙门的狰狞的天王力士,到底不过佣仆,云冈时期是毋需此等警卫保镖的。越明年,我又去河南,在洛阳市内走了一天,睡了一宵,满目民房、商店、工厂……油油荒荒,什么伽蓝名园的遗迹也没有——我想总归要怪自己,除非一旦成了考古学家,否则不必再到洛阳来。今寓海外,以为能免而竟亦不免偶兴去国离忧,在“哈佛”赋闲期间,燕京图书馆气氛寥落,临窗的乌木小桌上堆着大开本的书,是英译的《世说新语》,隔洋靴而搔国痒毕竟无济,便找原本,开卷即有魏晋人士影亦好之欢,见过人之后还想见见物,于是又翻《洛阳伽蓝记》,杨衒之欲为他所处的前后代作见证,是故“文”“史”夹杂,这种说明文有损于诗意的纯粹,有碍于品味其笔致的精妍,轮到现代人后代人(以后不断而来的青年们),恐怕都要由于不谙那段历史而忽略了这一大篇绝妙好辞。而且杨衒之似乎并未自认此“记”是散文诗,所以某些句某些字或有斟酌推敲的余地——我不再多想而尝试为之了:凡已成无谓的历史瓜葛者,节删之;凡文字对仗容许更工整者,剔饬之;凡太散文者,诗淬之;凡尤可臻于艺术的真实者,润色而强化之——故曰《洛阳伽蓝赋》,循例卒添一“乱”,乘势取《司马季主论卜》的那两句,萼结全赋,以抒感慨。在我的心目中,常把曹魏的洛阳比作东罗马的拜占庭,宗教、艺术、衣食住行,浑然一元的世界,已经近乎成熟的世界了,至少道理上是这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