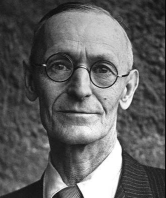一条路通向圣徒,通向精神殉道者,通向对上帝的自我献祭。另一条路通向纵欲之徒,通向欲望殉道者,通向对荒淫的自我献祭。市民们则生活于两者之间,试图谋求调和的中庸之道。他们从不自暴自弃,也绝不致力于献身,他们从不狂热,也从不苦修,永远不会成为殉道者,也绝不屈服于自我毁灭——他们的理想不是献身,而是自保。他们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圣性,亦不是神圣性的对立面。一切绝对性他们都难以承受。他们虽侍奉上帝,却也贪图享乐,虽志愿品行端正,却也要在尘世中享有轻松舒适。总之,他们试图安居于两种极端之间,安居于没有暴风骤雨的适度而有益健康的地带。他们成功做到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和感情的强度——追求绝对和极端生活之人才能赢得的强度。唯有牺牲“自我”才能活得强烈,市民们却珍惜“自我”胜于一切(当然只是发育不全的“自我”)。他们以牺牲生命和感情的强度为代价,实现了自保和安全。不是收获对上帝的狂热,而是收获良心的安宁;不是收获喜悦,而是收获惬意;不是收获自由,而是收获舒适;不是收获致命的灼热,而是收获宜人的温暖。因此,市民性的本质是生命驱动力的软弱。他们是胆怯的。他们唯恐付出自我,轻易接受掌控。为此他们以多数票替代权力,以法律替代暴力,以投票决议替代责任。